近日兩部主打懸疑推理、探案題材的網劇《白夜追兇》和《無證之罪》經常被拿來對比——不僅同期推出、題材相似,而且口碑也雙雙持續走高。連男主角都一樣是被驅逐出編制之外的前刑警,因為破案手段高明而作為顧問被請回刑警隊協助辦案。前者有潘粵明一人分飾兩角,可以大飆演技,后者則顏值比較高把一個蹲著馬桶玩著斗地主出場的史上最接地氣男主角演繹得自然又可愛(得虧是秦昊)。
現在兩部劇都已經播出過半了,各種反派角色也漸漸露出云遮霧障的部分真面目。單看對反派角色的塑造,對比之下如何呢?
《無證之罪》只有10集,只講一個連環殺人案,盡管牽涉的社會層面眾多、人物關系龐雜,但與男主角兩相較量的核心反派只有一個,就是姚櫓扮演的駱聞。

姚櫓飾演《無證之罪》反派駱聞
反觀《白夜追兇》,有32集的體量,據稱一共有8個案件,在已播出的16集里已經破獲了3個,而主線中牽扯到關宏宇關宏峰兩兄弟的2.13滅門案也穿插其中貫穿全劇,于是現在已知的重要反派就有3位個案兇手,和一位還沒露面的大boss。
第一個碎尸案,兇手是個腎病患者,殺了3個人,動機卻是:

“智商很高”? 確定?

當然,這個鍋有一半要表演來背;另一半,恐怕就要說到是本格推理的一個弱項——側重犯罪手法、推理過程的描述,而對犯罪動機、心理、社會因素等等則不太重視。
另一個案子也是一樣:“連環車震案”里,兇手每次都挑暴雨天氣中、在車里車震的一對男女下手、并且重復使用同一種作案工具;手法狠穩準,每次都會清理現場,不留一絲痕跡;作案后不急著逃逸而是會重新擺放尸體;反偵察能力極高,總能及時處理所有證據,還懂得向媒體泄漏作案細節,吸引他人模仿。作為慣犯,作案手段和心理素質都可以說很高了。
然而當他被審問時,是這樣的:
連環“車震”案兇手王志革,有嚴重強迫癥和潔癖,無法忍受他人觸碰
作案動機,是這樣的:

這個設定不是不可以成立,但要給出足夠的解釋、要自圓其說——比如為什么那種屈辱強烈到需要不斷殺人來緩解——否則就是一則無可理喻的天方夜譚,與觀眾遙不可及,心理上建立聯系更是無從談起。對于兇手犯罪心理機制的形成僅用寥寥數語帶過,用看似專業的術語來建立權威,對于觀看體驗不僅沒有幫助,反而制造疏離,重重隔重重。
唯一令人還有期待的反派大約就只剩下“霞姐”、“高騰”等人背后軍火走私集團的幕后大boss了。但懸念也僅僅集中在他/她為什么要陷害關宏峰、與警局內部有什么利益勾結等硬推理上,估計也依然會像其他幾位反派一樣,最大的存在感都在案情推理的臺詞描述里,而不是本人出場時,注定很難令人產生深刻的印象。
再來看《無證之罪》。反派駱聞從第一集就露面、第二集開始與男主角的正面較量,呈現出沉穩冷靜、理智縝密的個性和天才法醫的能力,四、五集開始逐漸明晰他尿毒癥晚期、原被害者家屬的悲劇經歷和殺人動機——即為了在有生之年內盡快找到謀害自己妻子女兒的兇手“雪人”,便模仿“雪人”的作案手段,不斷制造新的兇案,以促使警方加快動作尋找“雪人”。
“雪人”的作案特點
是不擇手段,也是為情所迫。這個動機不僅成立,而且幾乎是動人的——人人都能聯系自身,想象和代入失去至親的痛苦、和找到兇手的必要。于是觀眾對這類反派會產生同情、同理,在主角與反派的兩個對立立場之間搖擺掙扎(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我們簡直不希望男主角嚴良找到駱聞犯罪的證據),那么情感上的體驗就產生了烈度和記憶度。

駱聞向朱慧如坦白他的殺人動機
沒有人是天生的殺人魔,一切犯罪都是個人經歷與大背景、小環境、以及偶然性等種種因素交織在一起而誕生的。因此,一個犯罪故事里的反派角色,只有把他走上犯罪道路的動機和過程中逐漸強化的心理機制交代清楚、令人信服,才能算成功了一半——另一半則需要避免落入俗套,但那又是所有編劇們苦苦修行的另一大課題了,今天先按下不表。
話說回來,《無證之罪》里的反派角色之所以比《白夜追兇》更精彩,也是因為有了復雜的人性,和跌宕的命運感。從主角到反派,個個都亦正亦邪,每個人物也都在境遇之下變化著,有人會成長,有人會黑化——比如實習律師郭羽,從一個正直的愣頭青,在經歷了種種挫折、見識了社會的種種暗面之后,已經露出了黑化的跡象,下一集的懸念之一,就是看他如何應對黑化之后的種種麻煩。

黑化中的郭羽
如此長篇贅述,無非是想說說反派人物在塑造上的高明與平庸之別。有人總堅持本格推理與社會派推理應該分開來看待,確實應該承認兩派分別滿足了不同的趣味。但高明的故事應該要超越派別的局限。比方東野奎吾《嫌疑人X的獻身》與《惡意》兩部暢銷的本格推理小說,就做到了兼顧扎實推理分析的同時,把兇手的作案動機和心理講述得蕩氣回腸,在出人意料之外,回頭細細思索,又總能合乎情理,甚至讓讀者/觀眾對兇手產生同情和共鳴。
歸根結底,這是人物塑造的關鍵,不管是主角還是反派,每個行動都應該有足夠強烈并且合理的內驅力。如果人物不可信,故事怎么能夠站得住腳呢?
因此我始終相信,好的反派,不應該僅僅給人“扭曲”、“變態”、“難以想象”、“不可理喻”的印象、停留在驚悚獵奇的層面;而應該讓觀眾去逐層了解到這個反派的心理結構和心路歷程,他們應該是既可憎可怕,又可悲可嘆,甚至可以感同身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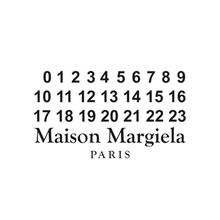



 粵公網安備44030702000122號
粵公網安備44030702000122號